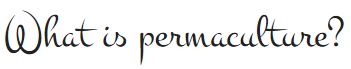
我从小就生长于塔斯马尼亚的小村庄,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皆是可以自己制作及生产。我们制作自己的长统靴,拥有自己的金属制品;我们捕鱼、种植食物、烘烤面包。 我知道,在这里居住的每个人,皆不只拥有一项工作,或是在这儿的任何事物皆无法仅是一项工作即可完成;每个人几乎都是同时从事好几项的工作。
从我小时候一直长大到约28岁的岁月里,还都不断怀抱着一个梦想。我将大部分的时间皆花在丛林或是在海上渡过,直至1950年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大部分已在逐渐消失中,才停止了此种生活方式。鱼群开始减少了,海岸线周边的海草变得稀疏了;大块面积的森林逐渐地消失。等到我发现我是多么地喜爱它们时,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我是如何地深爱我的家园。
数年后,我成为CSIRO野 生动物调查部门与塔斯马尼亚岛渔业部门的科学家,开始为了保护人类与其周遭环境而致力于反抗将会造成伤害的施政策略与工业发展体系。但很快地我认为持续地 保持对立,并不具有任何益处;因为,到最后通常并无法如愿成就任何事,于是我縠然撤出了社会抗争长达两年之久;我不想再去抗争任何事物,也不想再浪费任何 时间;我希望当我再度投入这个世界时,对一些事物仅会有正面的效果,而不会再使大家生活在有大规模生态系统崩解的环境里。于是从1968年起,我开始在塔斯马尼亚大学教书;其后,并在1974年时,与David Holmgren共同发展了一套永续农业栽培系统的架构;此套系统是以多年生乔木、灌木、草本(蔬菜及杂草)、蕈类及根菜类系统为发展基础;因而我创造了“永续栽培(Permaculture)”(即“朴门”)这个名词。我们花费了许多时间致力于永续栽培的一些原则确立及如何建立物种多样性的花园。直至1978年时,我们的努力终于达到巅峰,出版了第一本永续栽培的刊物,次年又接着出版了第二本同样的刊物。

大众对永续栽培的反应是混杂多样的。各专业领域的人表现出一些恼怒的情绪;因为我们将建筑与生物学、农业学与林业学、林业学与动物耕作学相结合在一起,使得自认为是各领域专家们皆感受到这种情绪;然亦有截然不同的受欢迎反应。因为过去有许多人皆以相同的方向思考,但他们对现今所实行的农业运作渐渐感到不满, 并盼望能够朝向更自然更生态的系统发展。
在1970年代,我所看到的永续栽培系统中,是属于人类居留地中有益的植物与动物社会之群聚;主要的目的在于朝向家庭与社区的自足,或许是仅能以此系统中所剩余的,才可能产生商业上的努力价値。
然而,永续栽培发展至现在,其实不只达到家庭食物的充分供给而已。因为仅是食物上的自足并不具有所有的意义,除非每个人皆获有接近土地、信息及财政资源的机 会。所以近几年来,永续栽培已发展至可涵盖适当的法律与财政策略;包含了土地间的路径链接、商业结构及区域性财政自足的策略。此种发展方式,即是要以能涵 盖整个人类系统而考虑。
直到1976年,我一直教授着永续栽培,然而却又于1979年,辞去了教职,并且将自己的高龄时光专注于不可知的未来;同时并决定将所有的时间与精力皆投入于尝试劝导人们的努力,以建立良好的生物系统。我设计了相当多的产物,并借着捕鱼及采摘马铃薯方式走过了不算短的一段时光。终于在1981年时,才有第一个受过地道永续栽培设计课程的硏究所学生毕业并开始着手设计澳洲永续栽培系统的工作。到如今(指1991年),全世界已有超过4000个毕业生,皆投入某些朝向环境保护与相关社会工作之行列。












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