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校长、现英国上议院议员Minouche Shafik总结说,20世纪的国际秩序是由两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塑造的。第一个历史时刻发生在 1945 年之后,当时通过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成立建立了当前的国际体系。第二个历史时刻发生在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
当今世界已大不相同。特朗普的治理逻辑是推动世界从基于规则的秩序转向交易逻辑治理,倾向于通过双边交易而非多边规则来处理国际事务。比如广泛批评多边机构,并利用其超强的实力和资源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提高其谈判实力,通过双边谈判或单边行动实现目标。
基于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预测未来十年全球风险集中在环境、技术和社会治理,以及个人判断全球治理转型、人工智能技术和特朗普新政加速旧国际秩序崩溃,Minouche Shafik发表在Project Syndicate的文章World Order in a Time of Monsters值得关注。
国家社会契约的失败,加上人们对国际体系明显不公平的日益愤世嫉俗和失望,加剧了全球秩序的崩溃。建立正和框架需要基于进步、安全和共同命运感的新社会契约。
伦敦 — — “旧世界正在走向灭亡,新世界正在挣扎诞生:现在是怪物的时代。”这句名言通常被认为是安东尼奥·葛兰西说的,在当今这个决定了上个世纪的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刻转变的时代,这句话显得尤为贴切。
这一秩序是由两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塑造的。第一个历史时刻发生在 1945 年之后,当时通过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成立建立了当前的国际体系。第二个历史时刻发生在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
自那时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全球高度一体化为特征的单极世界。塑造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则和规范得到了美国安全保障的支持,并植根于这样的信念:经济相互依存将克服地缘政治竞争并促进繁荣。
当今世界已大不相同。这是一个多极世界,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巴西、南非和海湾国家正在挑战旧秩序,其他新兴大国则要求在制定国际体系规则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与此同时,人们对“普世价值”和“国际社会”理念的信仰已日渐消退,许多人指出,富裕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囤积疫苗以及应对乌克兰战争的虚伪,与未能应对加沙、苏丹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道主义危机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
除这些压力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还威胁要撤销对欧洲和日本至关重要的安全保障,退出许多国际组织,并对朋友和敌人征收贸易关税。当该体系的担保人放弃它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可能正走向一个零秩序的世界,规则被权力取代——这对小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或者,它可能是一个由大型区域集团组成的世界,美国主宰其半球,中国统治东亚,俄罗斯重新控制前苏联国家。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更准确地反映我们多极世界的基于规则的新秩序。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旧秩序为何失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体系未能适应并给予它们足够的发言权,无论是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还是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投票权。在发达经济体中,一个被忽视的因素是国家层面的社会契约未能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社会契约——支撑国家凝聚力和政治稳定的规则、规范、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从家庭组织方式到如何应对失业、疾病和老龄化等挑战的一切。这些安排未能提供繁荣、安全和共同身份,在曾经作为旧秩序的缔造者和守护者的发达经济体中尤其严重。
期望的代际转变
国内社会问题以两种重要方式影响国际秩序。首先,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往往是同一个问题。劳动力市场受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和文化趋势通过大众媒体跨越国界,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结果。其次,人们对国内社会契约的态度会影响他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当个人感到繁荣和经济安全时,他们更有可能支持开放的经济和社会,并慷慨地对待国内和全球的不幸者。
矛盾的是,那些建立了全球秩序并从中受益最多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社会契约的最大压力,国内对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反对也最为强烈。经济学家往往难以理解这种动态,因为他们的职业根植于正和思想:国家从贸易中受益,竞争对消费者有利,提高效率的政策使社会变得更好。
经济学家不太擅长零和思维,即认为有人得利,就有人必定受损。这已成为近期政策制定的致命弱点,政策制定者没有充分关注分配问题,也没有考虑如何维持对正和经济政策的政治支持。
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调查问卷,询问父母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会比他们过得好还是过得差。在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父母绝大多数都认为他们的孩子会过得更差。相比之下,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情况恰恰相反。
这些预期是有数据支撑的。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千禧一代和X世代的实际收入几乎不高于他们父母同龄时的收入。他们往往负债更多,而且拥有房产的可能性更小。
在经济增长缓慢、社会流动性有限的时期长大的人更容易形成零和思维。随着发达经济体停滞不前、社会流动性下降,左翼和右翼对零和政治的支持都有所增加,助长了那些承诺保护选民免受外界威胁的领导人的崛起。
哈佛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四代美国人的零和思维的起源和影响。研究发现,“零和思维越强,人们就越支持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基于种族和性别的平权行动以及更严格的移民政策。”
这种思维可以追溯到个人及其祖先的经历,包括他们实现了多少代际向上流动性,他们是否移民到美国或生活在移民人口较多的社区,以及他们是否被奴役或生活在奴役率较高的地区。
新的社会契约
如果不首先修复国内社会契约,我们就无法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合作的、让所有人受益的全球秩序。当人们在国内缺乏安全和机会时,他们就会转向国内,担心竞争和移民。分裂和焦虑的社会成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私政治的沃土。相反,当经济蛋糕越来越大时,我们更容易慷慨地对待我们自己社会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弱势群体。对外援和国际政策协调的态度往往反映了这种动态,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更好的社会契约将扩大亚当·斯密所说的“同理心圈”,并促进更多的正和思维。但这样的秩序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关注三个关键主题:繁荣、安全和身份。
为了维持对世界的正和观,我们必须相信进步的可能性。调查显示,家长对孩子的未来前景持悲观态度,这基本事实显而易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环保主义者的“零增长”议程在政治上存在如此大的问题。
进步可以表现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物质改善。它也可以意味着福祉的提高,例如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更健康的身心健康、更健康的环境和更高的整体生活满意度。要使社会契约发挥作用,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善自己的命运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不满情绪往往在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很小或正在减少的国家和地区最为明显。
如今,在太多国家,人才被浪费,因为机会并非人人都能获得。这些被浪费的潜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出生在缺乏资源的家庭或社区的妇女和儿童,无法为他们提供机会。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社会中的人才?除了投资于生命早期,我们还应确保所有年轻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可能包括一笔终身捐赠,用于资助大学学习或职业培训,为个人可能更长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尽管大多数国家都为女孩和男孩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女性在职场上仍然处于不利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她们每天比男性多做两个小时的无偿劳动,包括家务和护理。更慷慨的育儿假、增加支持家庭的公共资金以及更公平的家庭分工将使社会能够更好地利用女性的才能。
此外,每个社会都可以设定最低收入水平,任何人都不能低于这个水平。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现金转移计划实现这一目标,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为低薪工人提供税收抵免实现这一目标。话虽如此,我仍然对任何能够提供有针对性福利的国家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持怀疑态度,因为把钱给那些不需要的人是低效的。
最低福利应包括基本医疗保健和足以防止老年贫困的国家养老金。它们还应涵盖病假和失业保险,无论雇佣合同如何。在发展中国家,这需要让更多工人进入正规部门。在发达经济体,这意味着要求雇主根据灵活工作工人的工作量向他们提供福利。
同样,我们社会中的许多风险本来可以更有效地分担或集体管理,但实际上却由个人承担。例如,如果工人知道他们将获得失业保险和再培训计划,在找到新工作之前为他们提供保障,那么雇主就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灵活地雇用和解雇工人。
儿童保育、医疗保健和养老等领域也需要进行类似的风险再平衡。例如,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雇主通常要承担产假的费用,而税收资助的育儿假可以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男女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减轻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负担。
同样,许多健康风险可以通过将风险集中到更多人群中并激励个人通过饮食和锻炼来缓解未来的健康问题来更有效地管理。自动加入养老金计划和老年护理保险将为个人在晚年提供更大的保障。日本和德国要求人们购买社会护理保险,这为集中管理此类与老龄化相关的风险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模式。
全球秩序重塑始于国内
正如经济学家对零和思维和分配问题关注不够一样,他们也往往低估身份的重要性。我曾经相信,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可以将社会重新团结起来,这一信念促使我写了《我们彼此欠什么》(What We Owe Each Othe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1 年)一书。然而,最近发生的事件让我改变了对身份在建立可行的社会契约中的作用的看法。
毕竟,身份认同是维系社会契约的粘合剂。已故民族主义学者埃内斯特·盖尔纳强调了共同的教育体系、文化同质化、共同语言和民族认同在塑造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性。瑞士和印度等不同国家表明,即使在多语言的联邦制中,也有可能培养民族认同。在多元化社会中,围绕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共同认同制定积极的议程尤其重要。
可以肯定的是,身份不是铁板一块,也不仅仅关乎种族或宗教。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受到教育、职业、性取向和个人兴趣等因素的影响。但共同命运的意识才是社会凝聚力的源泉,激励我们承担公民的责任,无论是纳税、遵守法律还是参与公民生活。
以移民为例——这可以说是欧洲和美国民粹主义政客提出的最突出的问题。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移民总体上有利于增长,但移民辩论很少涉及经济。相反,它以身份为中心: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是谁,以及何时应允许来自其他地方的人参与我们的社会契约。这就是为什么反移民言论经常关注移民或难民获得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的机会,这些被视为几代人通过贡献获得的福利。
我们正处于全球体系的根本性重组之中,其结果尚不明朗。我坚信,要实现正和博弈的国际秩序,就需要更强有力的国家层面的社会契约,以实现进步、安全和共同认同感。我们不能让那些以零和博弈、排他和自私的术语定义身份的人主宰全球叙事。通过解决这些国家问题,我们可以增加创建一个更公平的国际体系的可能性,为所有人带来更好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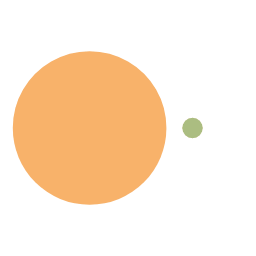














评论已关闭